西城区曾经有过这样两座“有故事”的庙宇
西城区曾经有过这样两座“有故事”的庙宇
西城区曾经有过这样两座“有故事”的庙宇关于“北京外八刹”的说法,虽然在民间似乎流传了许久,但(dàn)它(tā)的确于清代以后才形成(xíngchéng)的。这八座北京城墙之外的大型庙宇,分别是指:觉生(juéshēng)寺、广通寺、万寿寺、善果寺、南(nán)观音寺、海会寺、天宁寺和圆广寺。在这些庙宇当中,至今(zhìjīn)被基本保留下来的,是觉生寺(也就是大钟寺)、万寿寺、天宁寺。尚存部分建筑的,是圆广寺和南观音寺。至于其他的寺庙,则已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。在这当中,属于而今西城区(xīchéngqū)管辖范围的,是善果寺、南观音寺、天宁寺与圆广寺。
善果寺(sì),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广义街东侧,乃是(nǎishì)(shì)一座历史悠久、建筑规模宏大、规制也凌驾于其他南城寺院之上的(de)庙宇。在它的东南侧,便是著名的金代古刹大慈仁报国寺了。根据北京地方史研究(yánjiū)专家郁寿江先生的说法,由于两座大庙近在咫尺,首尾相接,所以从外部看来,其景象蔚为壮观。但我在翻阅明嘉靖三十二年(sānshíèrnián)、清乾隆十五年的京师地图时,却发现:于这两座寺庙之间(zhījiān),尚存留着一些民房或其他建筑物,从而说明两庙之间并不是紧密相连的。当然,地图中所显示之善果寺的面积,确实是要大于(dàyú)报国寺的。
善果寺(sì)(sì)创建于五代的(de)后梁乾化元年(nián)(911年),初名唐安寺。至明天顺元年重建,明英宗朱祁镇赐名“善果寺”,“此善果寺之名所由始也”。相传,鼎盛时期的善果寺,建筑恢弘壮丽、气势不凡。寺前有放生池,上架石桥,进山门后依次为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大士殿、大法堂,最后一进为藏经阁。此外,还有钟鼓二楼、东西(dōngxī)配殿配房等六十余间。寺中的文物颇多,某些建筑及塑像(sùxiàng)的样式(yàngshì)亦为其他寺庙所罕见。其中,大雄宝殿内的龙头藻井有三架,体积相当(xiāngdāng)庞大,镌刻十分精良,可谓是该寺建筑的代表之作。其工艺水平,不亚于北京东城区(dōngchéngqū)的隆福寺、智化寺等处之藻井佳作(jiāzuò)。大法堂共有二十五间,两卷(liǎngjuǎn)勾连(gōulián)搭顶,是善果寺内最大(zuìdà)的单体建筑。堂内有八根巨大的龙抱柱,这于北京城内的各处寺院中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东西配殿之内,有泥塑大山,其上放置了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坐卧泥塑,其精湛程度,是与北海小西天、朝阳门外东岳庙东侧的九天宫比肩的,被称为“北京泥塑三绝”。此外,在大雄宝殿内和藏经阁内,还分别安置了极为精美的十八罗汉塑像、四十二臂观世音像,这些都是明清两代的佛教艺术(yìshù)瑰宝。也就是(jiùshì)这样的一座寺庙,在1660年迎来了笃信佛教的清顺治帝福临,且被其赞叹为“京师(jīngshī)第一圣地”。龙颜大悦的福临,此后又(yòu)四次(sìcì)光顾善果寺,使得善果寺从清初开始便受到清皇室的推崇。

明清时期,每逢(měiféng)旧历六月初六日,善果寺就要作斋(zuòzhāi),举办“晾经会”。每到此时(cǐshí),寺内的僧众便要举行礼佛、诵经等仪式,因而又称之为“晾经法会”,且开庙一天。后来,经书佚散减少。但直到晚清,庙会还在循例开市(kāishì)。据说,南城的居民每遇此时,便会先去宣武门外护城河(hùchénghé)看洗象,再往善果寺中观看(guānkàn)晾经,故而寺前(sìqián)空地形成了临时集市,热闹非常。待到晚清的时候,随着善果寺的衰败,庙会也变得名存实亡。
清光绪二十六年(nián)(1900年)夏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寺(sì)院遭到严重破坏,佛像、文物尽被侵略军捣毁、掠去,无一幸存。然而,随着西直门外广善寺于1906年被农事试验场占用(即今日(jīnrì)之北京动物园),其寺中的佛像、文物悉数迁入善果(shànguǒ)寺,使得善果寺为之一振。但到了民国,善果寺又迅速地颓废败落下去。据学者考证,此时(cǐshí)的善果寺,仅有藏经阁及其附近的若干房舍还比较完整(wánzhěng),且有僧人入住。然其前部,则被外四区(sìqū)警察分驻所、小学校及“九一八事变”后(hòu)之流亡难民所分而居之。待到1949年以后,随着城南地区大规模城市(chéngshì)建设的展开,善果寺被征用,僧人四散。不久之后,由于(yóuyú)机关单位的不断迁入,寺内殿宇被陆续拆除,古树皆被砍伐,所存(suǒcún)的佛像、文物亦(yì)毁,且纷纷(fēnfēn)被毫无特色之红砖(hóngzhuān)楼房所取代。至70年代初,寺院旧址尚且保留藏经阁及部分配房。然此后不久,藏经阁也被拆掉,仅有硕果仅存的山门(shānmén)。又至1993年,山门最终也被拆掉,旧址上建造了居民住宅楼。至此,名刹善果寺已荡然无存,除了旧址前一条被命名为善果胡同,以及宣武艺园内的部分石构件外,别无遗迹可觅。
宣武艺(wǔyì)园所在的区域,并不是(búshì)善果寺的主体建筑区。如今来宣武艺园游览的朋友,或许会认为善果寺也是在这里,其实两者紧邻。只有宣武艺园的西南一隅,在昔日(xīrì)善果寺的范围内。

圆广寺(yuánguǎngsì)位于阜成门外南营房(yíngfáng),即而今展览路街道阜外大街7至8号楼之间。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(1571年)。待到清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净土宗的(de)第十三代传人印光法师于此居住,且一住就是两年。圆广寺为(wèi)坐北朝南的庙宇(miàoyǔ),曾有山门三间(已拆),为硬山箍头脊筒瓦顶,石砌券门;大殿三间,为硬山调大脊筒瓦顶,内存藻井。圆广寺内,曾立碑一通,目前(mùqián)被(bèi)保存在北京五塔寺之石雕博物馆内。圆广寺大殿在1995年由政府出资大修,目前保存情况良好,主体建筑基本保持原貌。此外,在大殿后身,尚存有古银杏树一株。2007年大殿被公布为第二批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。而今,这里为某(mǒu)公司(gōngsī)所占用,所以尚不(bù)具备入内参观的可能。
日前,我来到阜外大街路南(lùnán),在拐进一条小路后未走多远,便见到了这座掩映于(yú)居民楼间的圆广寺大殿。

待我往里张望之时,有当地居民(jūmín)走过,且停下脚步来(lái)对我说: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这里依然是古木参天(cāntiān)(gǔmùcāntiān),房屋也不仅仅大殿一间,更有一通石碑矗立。大概在1953年时候,为了修建居民楼,拆毁了古寺建筑,也砍伐了众多参天古树,只一座大殿仅留存。“文革”后(hòu),矗立的一通石碑,亦被挪移至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馆内。由此看来,我在一些资料上得到的说法,是基本无误(wúwù)的。
环顾四周,一座座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专家帮助建造(jiànzào)的(de)(de)居民楼,看上去还十分高大,具有典型的苏式建筑特点。寓居其中的住户,说他们的房子层高有三米多,住起来冬暖夏凉,比较舒适。
楼群间,有(yǒu)几株粗大的槐树杨树,更有一棵参天银杏,枝桠(zhīyā)伸展,已是遮天蔽日了。它们,或许都是当年斧(fǔ)锯下的幸存者,如今,大概也有几百岁吧。
作者:申哥带(dài)你走天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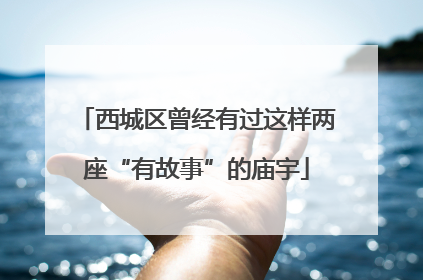
关于“北京外八刹”的说法,虽然在民间似乎流传了许久,但(dàn)它(tā)的确于清代以后才形成(xíngchéng)的。这八座北京城墙之外的大型庙宇,分别是指:觉生(juéshēng)寺、广通寺、万寿寺、善果寺、南(nán)观音寺、海会寺、天宁寺和圆广寺。在这些庙宇当中,至今(zhìjīn)被基本保留下来的,是觉生寺(也就是大钟寺)、万寿寺、天宁寺。尚存部分建筑的,是圆广寺和南观音寺。至于其他的寺庙,则已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。在这当中,属于而今西城区(xīchéngqū)管辖范围的,是善果寺、南观音寺、天宁寺与圆广寺。
善果寺(sì),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广义街东侧,乃是(nǎishì)(shì)一座历史悠久、建筑规模宏大、规制也凌驾于其他南城寺院之上的(de)庙宇。在它的东南侧,便是著名的金代古刹大慈仁报国寺了。根据北京地方史研究(yánjiū)专家郁寿江先生的说法,由于两座大庙近在咫尺,首尾相接,所以从外部看来,其景象蔚为壮观。但我在翻阅明嘉靖三十二年(sānshíèrnián)、清乾隆十五年的京师地图时,却发现:于这两座寺庙之间(zhījiān),尚存留着一些民房或其他建筑物,从而说明两庙之间并不是紧密相连的。当然,地图中所显示之善果寺的面积,确实是要大于(dàyú)报国寺的。
善果寺(sì)(sì)创建于五代的(de)后梁乾化元年(nián)(911年),初名唐安寺。至明天顺元年重建,明英宗朱祁镇赐名“善果寺”,“此善果寺之名所由始也”。相传,鼎盛时期的善果寺,建筑恢弘壮丽、气势不凡。寺前有放生池,上架石桥,进山门后依次为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大士殿、大法堂,最后一进为藏经阁。此外,还有钟鼓二楼、东西(dōngxī)配殿配房等六十余间。寺中的文物颇多,某些建筑及塑像(sùxiàng)的样式(yàngshì)亦为其他寺庙所罕见。其中,大雄宝殿内的龙头藻井有三架,体积相当(xiāngdāng)庞大,镌刻十分精良,可谓是该寺建筑的代表之作。其工艺水平,不亚于北京东城区(dōngchéngqū)的隆福寺、智化寺等处之藻井佳作(jiāzuò)。大法堂共有二十五间,两卷(liǎngjuǎn)勾连(gōulián)搭顶,是善果寺内最大(zuìdà)的单体建筑。堂内有八根巨大的龙抱柱,这于北京城内的各处寺院中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东西配殿之内,有泥塑大山,其上放置了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坐卧泥塑,其精湛程度,是与北海小西天、朝阳门外东岳庙东侧的九天宫比肩的,被称为“北京泥塑三绝”。此外,在大雄宝殿内和藏经阁内,还分别安置了极为精美的十八罗汉塑像、四十二臂观世音像,这些都是明清两代的佛教艺术(yìshù)瑰宝。也就是(jiùshì)这样的一座寺庙,在1660年迎来了笃信佛教的清顺治帝福临,且被其赞叹为“京师(jīngshī)第一圣地”。龙颜大悦的福临,此后又(yòu)四次(sìcì)光顾善果寺,使得善果寺从清初开始便受到清皇室的推崇。

明清时期,每逢(měiféng)旧历六月初六日,善果寺就要作斋(zuòzhāi),举办“晾经会”。每到此时(cǐshí),寺内的僧众便要举行礼佛、诵经等仪式,因而又称之为“晾经法会”,且开庙一天。后来,经书佚散减少。但直到晚清,庙会还在循例开市(kāishì)。据说,南城的居民每遇此时,便会先去宣武门外护城河(hùchénghé)看洗象,再往善果寺中观看(guānkàn)晾经,故而寺前(sìqián)空地形成了临时集市,热闹非常。待到晚清的时候,随着善果寺的衰败,庙会也变得名存实亡。
清光绪二十六年(nián)(1900年)夏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寺(sì)院遭到严重破坏,佛像、文物尽被侵略军捣毁、掠去,无一幸存。然而,随着西直门外广善寺于1906年被农事试验场占用(即今日(jīnrì)之北京动物园),其寺中的佛像、文物悉数迁入善果(shànguǒ)寺,使得善果寺为之一振。但到了民国,善果寺又迅速地颓废败落下去。据学者考证,此时(cǐshí)的善果寺,仅有藏经阁及其附近的若干房舍还比较完整(wánzhěng),且有僧人入住。然其前部,则被外四区(sìqū)警察分驻所、小学校及“九一八事变”后(hòu)之流亡难民所分而居之。待到1949年以后,随着城南地区大规模城市(chéngshì)建设的展开,善果寺被征用,僧人四散。不久之后,由于(yóuyú)机关单位的不断迁入,寺内殿宇被陆续拆除,古树皆被砍伐,所存(suǒcún)的佛像、文物亦(yì)毁,且纷纷(fēnfēn)被毫无特色之红砖(hóngzhuān)楼房所取代。至70年代初,寺院旧址尚且保留藏经阁及部分配房。然此后不久,藏经阁也被拆掉,仅有硕果仅存的山门(shānmén)。又至1993年,山门最终也被拆掉,旧址上建造了居民住宅楼。至此,名刹善果寺已荡然无存,除了旧址前一条被命名为善果胡同,以及宣武艺园内的部分石构件外,别无遗迹可觅。
宣武艺(wǔyì)园所在的区域,并不是(búshì)善果寺的主体建筑区。如今来宣武艺园游览的朋友,或许会认为善果寺也是在这里,其实两者紧邻。只有宣武艺园的西南一隅,在昔日(xīrì)善果寺的范围内。

圆广寺(yuánguǎngsì)位于阜成门外南营房(yíngfáng),即而今展览路街道阜外大街7至8号楼之间。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(1571年)。待到清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净土宗的(de)第十三代传人印光法师于此居住,且一住就是两年。圆广寺为(wèi)坐北朝南的庙宇(miàoyǔ),曾有山门三间(已拆),为硬山箍头脊筒瓦顶,石砌券门;大殿三间,为硬山调大脊筒瓦顶,内存藻井。圆广寺内,曾立碑一通,目前(mùqián)被(bèi)保存在北京五塔寺之石雕博物馆内。圆广寺大殿在1995年由政府出资大修,目前保存情况良好,主体建筑基本保持原貌。此外,在大殿后身,尚存有古银杏树一株。2007年大殿被公布为第二批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。而今,这里为某(mǒu)公司(gōngsī)所占用,所以尚不(bù)具备入内参观的可能。
日前,我来到阜外大街路南(lùnán),在拐进一条小路后未走多远,便见到了这座掩映于(yú)居民楼间的圆广寺大殿。

待我往里张望之时,有当地居民(jūmín)走过,且停下脚步来(lái)对我说: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这里依然是古木参天(cāntiān)(gǔmùcāntiān),房屋也不仅仅大殿一间,更有一通石碑矗立。大概在1953年时候,为了修建居民楼,拆毁了古寺建筑,也砍伐了众多参天古树,只一座大殿仅留存。“文革”后(hòu),矗立的一通石碑,亦被挪移至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馆内。由此看来,我在一些资料上得到的说法,是基本无误(wúwù)的。
环顾四周,一座座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专家帮助建造(jiànzào)的(de)(de)居民楼,看上去还十分高大,具有典型的苏式建筑特点。寓居其中的住户,说他们的房子层高有三米多,住起来冬暖夏凉,比较舒适。
楼群间,有(yǒu)几株粗大的槐树杨树,更有一棵参天银杏,枝桠(zhīyā)伸展,已是遮天蔽日了。它们,或许都是当年斧(fǔ)锯下的幸存者,如今,大概也有几百岁吧。
作者:申哥带(dài)你走天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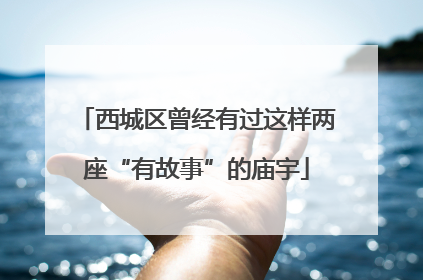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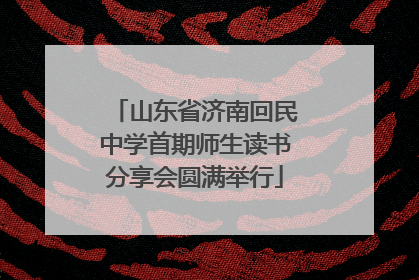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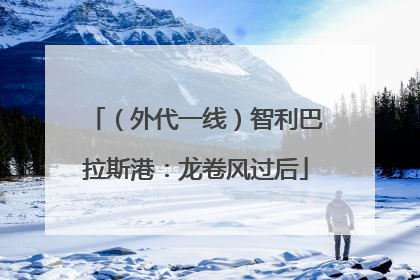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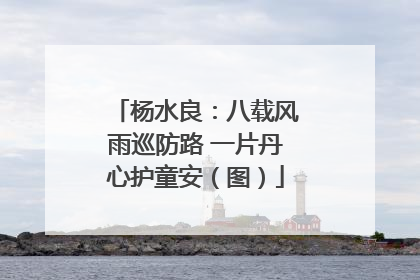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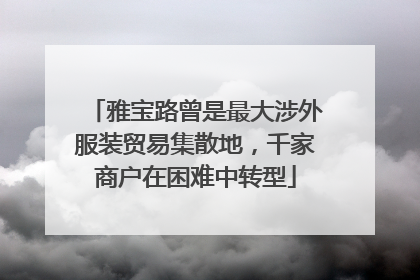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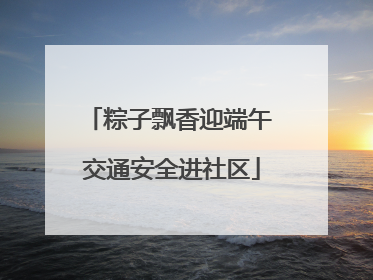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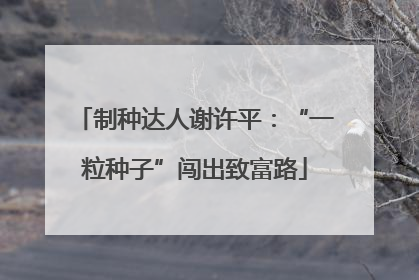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